来源:资管网
4月4日,市场监管总局消息,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涉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,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杜邦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立案调查。
曾记否,那些年,杜邦的黑历史?
致命渗透: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化学骗局
1998年,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农民坦南发现,自家牧场的牛群接连死亡:肿瘤、牙齿乌黑、胆囊肿胀,甚至发疯攻击人类。这场诡异的灾难,最终指向了杜邦公司填埋场的化学废弃物——全氟辛酸(PFOA)。
杜邦早在1950年代便知PFOA的毒性。内部实验显示,这种物质会导致动物肝脏病变、基因缺陷,甚至致癌。然而,凭借美国环保局对新兴化学品监管的空白,杜邦选择隐瞒真相,将含有PFOA的废水排入俄亥俄河,污染了数十万居民的饮用水源。直到2001年,律师罗伯特·比洛特通过一场长达17年的诉讼,才揭开了这场“化学谎言”:杜邦内部文件显示,公司不仅长期掩盖风险,甚至参与制定“安全浓度标准”以逃避追责。2017年,杜邦以6.71亿美元与3500名受害者和解,但健康与生命的代价已无法逆转。
资本的贪婪往往披着创新的外衣。杜邦的‘化学帝国’建立在公众健康的灰烬之上,而真相的揭露,不过是冰山一角。

军火发家与原罪积累:从战争财到道德塌陷
杜邦的崛起始于火药。1812年美英战争期间,其硝酸钠配方火药因爆炸力强劲成为军方宠儿,南北战争时更售出400万磅火药,攫取巨额利润。一战期间,杜邦凭借垄断地位成为全球最大军火商之一,甚至被戏称为“死亡商人”。
但军火生意的道德困境远未结束。20世纪中叶,杜邦将目光投向化工领域,推出尼龙丝袜等消费品,却以另一种形式延续“毒性遗产”。其生产的聚四氟乙烯(特富龙)因PFOA污染问题,再次将企业推向伦理审判席。
从火药到尼龙,杜邦的每一次转型都踩中时代风口,但风口之下,是无数被牺牲的‘沉默大多数’。
技术创新背后的代价:垄断与生态掠夺
杜邦以“创新”自诩,但其技术跃进往往伴随生态劫难。20世纪初,公司通过兼并同行、组建行业托拉斯,垄断美国火药市场。二战后转型化工领域时,又通过数据操控和资本游说,将有毒化学品的生产合法化。
更讽刺的是,杜邦在中国市场仍被奉为“座上宾”。江苏常熟的聚四氟乙烯工厂自2005年投产以来持续扩张,而PFOA的阴云始终未被彻底驱散。
技术的进步若缺乏敬畏,便成了资本扩张的凶器。杜邦的全球产业链,实为一场‘污染转移’的精致算计。
家族帝国的暗面:近亲通婚与权力游戏
杜邦家族的统治史同样充满争议。为保持财富与权力不“外流”,家族长期推崇近亲通婚,甚至将不合格者逐出核心圈。20世纪初,科里·杜邦抛售股票引发内部危机,最终靠皮埃尔等人“内部抄底”才保住控制权。这种封闭的治理模式,虽维系了商业帝国,却也滋长了傲慢与短视。
家族企业的传承,若以血缘为壁垒、以利益为唯一准则,终将沦为道德真空的‘孤岛’。
黑水未尽,资本何往?
杜邦的故事,是工业文明与人性博弈的缩影。从火药到特富龙,从军火暴利到化学骗局,其“黑历史”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: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血与火,而企业的社会责任,常在与利润的较量中败下阵来。
正如电影《黑水》所警示:“没有人是局外人。”当跨国资本以“发展”之名行掠夺之实,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法律的铁拳,更是对技术伦理的深刻反思。
企业的伟大,不应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。杜邦的教训,当为所有追逐“创新神话”的后来者敲响警钟。
(本文部分史实援引自《黑水》事件纪录片及杜邦公司历史档案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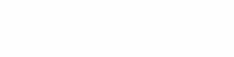

评论列表